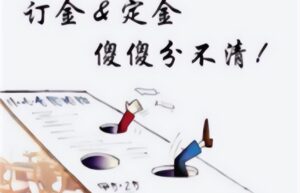环卫猝死认定算工伤吗(猝死工伤赔偿标准)
羲之路在山东临沂的城市中心,穿过人民广场后,向南延伸,在银雀山路与启阳路之间被截出一段290米长的生活街道。因为几天前刚下过一场大雪,没来得及清理的积雪被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轧成一层锃亮的冰,走在上面得格外小心。
因为临着几个老小区,这条路分布着水果摊、猪肉铺、卖家禽的摊子、山东煎饼铺等几十家商铺,构成一个条状的农贸市场。商铺多,产生的生活垃圾也多,因此,路上一共设了两个垃圾站点,分别在路的两端,每个站点集中放着八九个一米来高的绿色垃圾箱。老韩在这条街上卖了20多年的猪肉,他的店铺和朝南的垃圾站点仅隔一条马路。2020年12月29日,刘汝祥倒下时,他是第一个跑过来的。
刘汝祥生于1951年,是羲之路上的环卫工。因为已经在这条街上干了一两年,周围商铺的老板都认识他,平时都喊他老刘。12月29日早上5点多,天还没亮,老韩与老婆来店里准备当天的货品,刘汝祥已经像往常一样在扫街了。老韩的老婆与刘汝祥打招呼:“这么冷的天,还来这么早啊?”刘汝祥应和着,夜色中看不出神色有什么异样。

(视觉中国供图)
这天是2020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三天前,中央气象台就发布消息,称12月28日~31日,“今冬最强寒潮”(注:2020年)将从西北、华北等地开始,一路扩张南下,降温范围覆盖整个中东部。大部分地方一天内降温达到10摄氏度以上,而且最低气温在5摄氏度以下,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12~14摄氏度。
临沂是在12月28日下午14时许发布的寒潮黄色预警,十几个小时后,临沂的气温从前一天的最高温9摄氏度直降至最低温零下11摄氏度,伴随着鹅毛大雪和五级大风。老韩对那天的冷记忆犹新,他告诉我,虽然穿着和前一天一样的棉服,但明显感觉不够用了,“手指头都伸不直,耳朵也要冻掉了”。
相隔不远的另一家肉铺的老板称,铺子里的水表那天被冻裂。寒潮以及伴随的大雪也在全市范围内引发预警,临沂的大部分中小学、幼儿园在这天停课。临沂汽车客运总站所有班线早上6点多开始停止发车,临沂境内部分高速封闭。
当整个城市因为寒潮的到来而放缓运转时,环卫工人却需要提前开工。临沂环卫集团的一名后勤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当地环卫工一般是在早上6点开始工作,但遇到落叶较多或清雪除冰的情况,环卫工需要在清晨4点就上班,以保证几个小时后的上班高峰期道路顺畅。
刘汝祥的日常上班时间比其他人还要早一些,和他一个环卫小组的工友老马告诉我,环卫工的工作是多劳多得,有些环卫工希望多赚点,就会向公司申请承包更长的路段,工作时间只能自行提前。刘汝祥负责的路段有290米左右,但因为商铺多,生活垃圾多,工作量大。再加上街面上来往车辆一多起来,垃圾被吹得满天飞,更不好清扫,因此刘汝祥一般在凌晨3点多起来工作。
12月29日这天也不例外。凌晨3点多,刘汝祥离开了自己的出租屋。此时已经下起雪来,他穿着短款棉袄,外面套黄色的环卫制服。或许是因为下雪,他又在工作服外套了件有环卫标志的长雨衣,脚上是一双长及小腿的油鞋。
环卫工的工作时间一般分三个阶段:凌晨到早上7点半,然后是早饭时间,8点半再上岗,继续工作到11点半下班,下午13点半上班,17点半下班。那天上午8点多,吃完早饭,老马出门去上工,路过刘汝祥的出租屋时,看到对方正拿着铁锨站在门口,老马喊了句“到点了,走吧”,刘汝祥以正常的语气应和着,“走啊,走啊”。
这天更早的时间,公司负责考勤的临沂环卫集团路段管理员辛凤菊也曾与刘汝祥打过一次招呼,隔着老远的距离,刘汝祥对她露出笑容。

(朱万昌 摄/视觉中国供图)
刘汝祥是在上午8点30分左右倒下的。当时,因为下雪,路上的行人比往日要少一些。老韩在猪肉铺里向外张望,突然看到正背对着他翻捡垃圾桶的老刘直直地往后倒,还没等老韩反应过来,他已经全身着地,帽子从头上脱落。老韩大喊一声“老刘!”,没反应。他扔下铺子,赶紧跑过来察看。
此时,老刘的双眼闭着,脸通红,嘴巴张着,向外捯气儿。蜷曲的右手还握着刚从垃圾桶里捡到的一把菜刀,刀锋挨着脑门,在脑门上划出一道细小的口子。左手则平伸在身体一侧,两腿蹬得笔直。隔壁肉铺的老板和几米之外的小区门卫周师傅也被惊动,陆续跑过来,但谁也不敢轻易挪动他。8点42分,老韩拨出第一个120电话,此时雪越下越大,几个人找来一块塑料布,盖在刘汝祥的身上,以防他被大雪淋湿。
积雪路滑,救护车比平时来得慢些。8点53分,老韩再次拨打120时,对方告知还在路上。直到上午9点,救护车才赶到,此时“老刘的身子都已经硬了”,老韩说。一天后,刘汝祥所属的公司临沂环卫集团发布通告,初步诊断为突发心脏病死亡,具体死因需由法医进一步鉴定。
直到刘汝祥突然离开,老马才想起,就在半个月前,公司组织的一次常规体检中,医生告诉刘汝祥血压有点高,需要注意。而在更早的两个多月前,刘汝祥还告诉他,自己感冒了,老咳嗽,喘不上气。老马劝他去开点感冒药,环卫工没有休息日,所以工友们有点小病小痛,一般都是去药房拿点药,很少专门跑去医院。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刘汝祥的咳嗽、气喘似乎一直未见好,老马以为是抽烟的缘故,还劝他少抽点。门卫周师傅也听刘汝祥提起过自己的“感冒”。事发当天帮忙看守刘汝祥的另一位肉铺老板告诉我,最近这段时间,见到刘汝祥,觉得“他干这活儿,有点怪累的感觉”,具体表现在哪儿他也说不上来,但和妻子闲聊说起时,妻子反驳他:“年龄大了,干这活儿还能不累吗?”
谁也没把这些微不足道的异样放在心上。相比于自己的身体,刘汝祥更关心的可能是临近的春节。他是2020年疫情之后来临沂的,已经8个多月没回家看看了。他告诉老马,准备干到腊月二十,不管公司放不放假,他都要回家过年。
从村庄到城市刘汝祥的老家在新泰市羊流镇雁翎关村,距离临沂约140公里。从临沂市坐大巴再转出租车,3个小时就可到达。依照大多数传统的乡村习俗,刘汝祥在村里时和儿子家住一起。那是农村常见的两层自建楼,屋子里虽然装修简陋,但从外观看挺气派,外墙上贴着瓷砖,门楼做了拱形挑高设计。
2020年12月29日接到老马打来的电话时,刘汝祥的儿子刘军正在安徽打工,女儿刘凤已经外嫁到相隔几里的邻村,虽说人在村里,但那天的雪太大,市区的所有客运车辆停运,直到下午,才联系到一辆私家车去临沂。等两个人都赶到时,已经是傍晚了。
姐弟俩在临沂待了三天处理父亲的后事,临走时带了一只公鸡和纸钱,来到父亲倒下的地方。在他
们老家,有公鸡叫魂的说法,可以将死在他乡的长辈的魂魄牵引回故里——在外漂泊大半生的刘汝祥最终以这种方式回到了家乡。
在刘凤的印象里,自己3岁时,父亲就离家远去东北,在当地生产队打工,开荒垦田。他走后不久,家里就出了意外,年三十那天,3岁的刘凤将脸杵到了正在烤肉的柴火炉子里,脸被大面积烧伤。父亲赶不回来,母亲既要下地干活儿,又要带着刘凤一趟趟跑医院。当时,村子到镇上不通车,需要走路过去,母亲在那一年的时间里,受尽辛苦。等到脸上的伤治得差不多了,刘凤的姥爷将母女二人送上了前往东北的火车。

(视觉中国供图)
在东北的8年里,刘汝祥和妻子一起,在黑土地上种土豆、南瓜、豆角。刘汝祥勤奋,脑子活络,在生产大队挣工分之余,做过不少副业,比如帮别人家劈柴,或是自己卷一些烟草拿去集市上卖。刘凤记得,有一年除夕前夜跟着父亲去卖黄烟,两个人上个厕所的工夫,烟草就被人偷了,那年春节,年货就略显寒酸了——只买了3斤猪肉。但父亲勤劳,再加上那时的东北好落户,很快刘汝祥就在当地盖了自己的房子。
一转眼,刘凤已经11岁。老家的习俗是,女儿18岁左右就要张罗着嫁人的事了。刘汝祥内心深处还是希望一家人能回到自己的故乡,在老家为女儿择一个好人家。于是,他卖了在东北的房子和家当,拿着6000元钱,带着刘凤母女又回到了羊流镇。
回到老家,刘汝祥对种地的兴趣已经不高。在外漂泊多年,他已经发现,只要勤快活络,不怕脏累,当一个城市中的流民,从工业的缝隙里获取收入,哪怕只是零零星星,也比老老实实做一个村庄里的农民赚得多。他先是干起拉煤的活计,4年后再次带着女儿北上,去黑龙江的砖窑里烧砖、砸铁,到牡丹江里淘沙,还短暂地去过上海的建筑工地打工,顺利的时候,半年就可以赚2000块钱。
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农村刚开始实行土地包产到户,很少有人扔下村里的田地外出打工。刘汝祥算是村里的“异类”。
因为肯卖力气,和刘汝祥共事过的人都喜欢再找他干活儿。上世纪90年代,一个曾经雇过他的老板又将他介绍到河南的一个工厂里帮忙砸铁,从此,刘汝祥在河南一待就是二十几年。辗转过周口、开封、信阳等地,去过汽车厂、铸造厂、拖拉机厂等,刘汝祥后来组建起一支十几人的小包工队,什么散活儿都接。哪家厂里的设备坏了,修起来很麻烦,刘汝祥就带人去修好;也有厂里的铸铁件生产不合规,需要回炉重造,刘汝祥就带着人去帮着把这一堆报废器械拆开、砸碎,按吨数分工钱,“好比一吨20块钱,这堆东西有5吨,三个人一起干,那挣的100块就三个人分”。
刘军说,他当时也辍学加入了父亲的队伍,承包的很多活儿都是厂子里的正式工不愿意干的。“厂子里的正式工一天能挣200块工资,不愿意挣那500块的,因为太累了。但是话说回来,不辛苦的话,人家厂子里也不会用你来干。”

(视觉中国供图)
那段时间正是中国制造业大发展的时期,工人地位高,厂子效益好,刘汝祥这个小小包工队的收入也在与日俱增。最好的时候,他可以给工人开到一个月六七百元的工资,自己每月则能赚小1000块。年轻、有用不完的力气,钱如涓涓细流,源源不断地进入口袋,那是刘汝祥一生中最意气风发的时候。20多年在外务工的生涯里,刘汝祥攒下了20多万元,花11万元给儿子盖了新房,娶了媳妇。
几十年卖力气挣来的一点积蓄,花起来却如流水般快。刘军记得家里的经济状况是从2000年母亲去世时开始变差的。那年,母亲50岁,患肝癌,彼时农村还没有实行医保政策,在当地县城看病,几万块医药费都要自己承担。不到一年,母亲就撒手人寰。事实上,母亲的病不是突然得的,她有8年的肝硬化史,常年药物不断。好在那时候,40多岁的父亲还可以拿力气换钱,并不觉得有多大的负担。上了50岁后,当可以卖的力气都用完,钱开始像沙漏一样往外漏。
刘汝祥的右腿也在一次做工中受了工伤,股骨头断裂,做了两次手术,一共花了三四万元。虽然痊愈,但从此以后,右腿开始一瘸一拐,使不上力。再加上进入2000年后,此前包工的小厂倒闭的倒闭、亏损的亏损,很难再接到活儿。
刘汝祥回了老家,用手上仅剩的一点钱给儿子买了面包车,用来拉客。“他那个意思就是,以后咱不出这么大的力了,就在家干点轻松的活儿。”刘军说。但面包车拉客的生意并不好,一年后,刘军就把父亲的车卖了,和妻子一起去了临沂,做一些回收废品的工作。现在,他在安徽的一家厂里当吊车司机,每月有大约6000元收入。
儿子离开村庄后,刘汝祥在老家买了个三轮车,进些菜来卖,但受伤的腿一蹬车就疼,干了两年就干不动了。没过多久,他从老家跑了出来,打算去城里继续找点不用那么费力的活儿干。这次离家时,刘汝祥已经61岁。
回不去的家老马与刘汝祥相识于2017年左右,那已经是刘汝祥来临沂几年后了。当时,老马在沂蒙路上扫街,刘汝祥还在马路边的一个居民小区里当门卫,二人听对方都是山东口音,一来二去就熟了起来。刘汝祥告诉老马,在此之前,自己曾在一家职业技术学校兼职干过门卫和保洁。
2019年上半年,刘汝祥的兄弟生重病,刘汝祥辞掉工作回了老家,在家里待了几个月,一直到把兄弟送终才又回来。等再去原来的单位求职,对方已经不要他了,理由是对于门卫这个岗位,刘汝祥的年纪已经超龄。老马想到,羲之路的一个路段,原来的环卫工老石因为年纪大又生病辞职,他不干后那条街一直没找到人扫。老马将刘汝祥介绍给临沂环卫集团,2019年下半年,刘汝祥入职。
此时,刘汝祥已经68岁,以这个年龄,环卫工可能是他在城市里少有能找到工作的工种。临沂环卫集团的一名后勤工作人员告诉本刊,公司里做环卫工的都是合同制,年龄都偏大。该工作人员的解释是,环卫工工资不高又累,年轻一点的人宁愿选择保安、服务员这类工作,最后只能招到五六十岁的。

(视觉中国供图)
负责考勤的路段管理员辛凤菊手下管着八九个环卫工人,这些人里年纪最大的已经80多岁,最小的也58岁。老马今年68岁,老家在山东临沂市下面的一个村子,早年间是村里的民兵连成员,开过山洞,还参加过唐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后来,入党成了党员,当了27年的村干部。退休后,每个月的干部补贴和农村养老保险加起来不到600块,还要帮两个儿子在保定买房,他就追随已经在临沂环卫集团打工的老伴而来,一干就是十几年。
公开资料显示,临沂环卫集团是临沂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0年。集团的人员数量在500~1000人左右。老马虽然在这里一干十几年,但一直是合同工,也没有社保。事实上,辛凤菊手下的这几个环卫工里,只有老赵是有社保的。
老赵是队伍里最年轻的,今年58岁,2017年来临沂环卫集团,现在负责一段160米长的街道,每个月工资1600元,加上加班费,可以拿到2100元左右。每个月他自己会出380元的社保,公司再帮他缴纳一部分。老赵的家也在临沂下面的农村,早年间在临沂做搬家工,年纪大了干不动了之后,找了这份环卫工的工作。老赵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和他一起生活在两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平房里,两个人都有智力问题,他想,以后即使干不动了,至少可以凭借这份社保领退休金,保障一家人的生活。
在这个8人的环卫工小组里,老赵的故事并不特殊。一位来自临沂河东区农村的阿姨告诉我,她今年60多岁,老伴几年前得了膀胱癌,现在靠高额的医疗费续命,家里已经借了十几万的外债。几年前,她在环卫作业时掉入下水道,伤了膝盖,现在必须要借助外物才能站立。于是扫地时,拖把就是她的拐杖;铲雪时,铁锹就是拐杖。我们聊天的那个下午,在附近打工的儿媳妇骑着电动车来为她送了双棉油鞋,8块钱买的,方便她在大雪天里活动。
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大厂青年的过劳猝死,这群流浪在城市的乡村老人,同样在用自己暮年残弱的身体,挑起生存的重担。凌晨两三点上班、下午17点半下班是不少环卫工的工作常态,遇到雨雪等特殊的天气还要加班。1月1日元旦这天,已经下班回家的路段管理员辛凤菊突然又骑着电动车返了回来,紧急叫住还没走的几个环卫工。她告诉我,刚接到经理的通知,银雀山路部分路段的雪水过多,需要清理一下。环卫工们把收起的工具又拿了出来,开始埋头铲水。辛凤菊拍照打卡,发到工作群里。等到干完活儿,已经是将近18点。
对“老无所依”的恐惧出现在每个环卫工的言谈举止里,拼命攒钱才能带来些许的安全感。刘汝祥有一张专门收工资的银行卡,当他去世后,刘凤在他的出租屋里找到了这张卡,里面是他这几年在临沂的全部工资收入,几乎一分未动。老马告诉我,刘汝祥在做环卫工之余,会捡点破烂卖,每天能赚20多块,卖破烂的钱就是他全部的生活开销。但刘汝祥生活节俭,经常买几个大馒头就是一顿饭了,也几乎不买衣服,穿的大都是直接从垃圾桶里捡来的。当为父亲收拾出租屋时,刘凤发现,父亲卖破烂的收入所得还存下了将近六七百块钱,都是一块、十块的面额,装在一个铁盒子里。
那是刘凤第一次来父亲在临沂的出租屋。屋子不到15平方米,一张横放的单人床已经占据了三分之一的空间。床头紧贴着一张木头桌子,上面放着一个保温杯,是刘汝祥参加一次社区活动时赢得的赠品。桌子的一端紧挨着另一张长桌,上面放了些杂物。做饭区在床尾方向,有几个不锈钢锅具和一个小电炉。靠近窗户的位置被刘汝祥绑了根晾衣绳。屋子里没有取暖设备和火炉,不知道刘汝祥原本打算如何度过这次寒潮。

(插图 老牛)
刘凤不止一次在电话里劝父亲回家,刘汝祥每次都告诉她,在城里待着“自在”。对在外游荡了半生的父亲来说,那个农村的家是几近陌生的。因为常年离家,“同辈人里,没有关系特别好的”,反而在这个距家100多公里远的城市里,他还交到一些朋友。他们大多同样是流浪在城市里的乡村老人,有着相互理解的境遇和心思。
刘汝祥和老马租的房子在一个胡同,相隔十几米远,经常约着一起上班。他总去街道上的一家羊肉汤馆买羊汤喝,汤馆的大姐有时会把卖不完的包子和汤免费送他,拿回来可以喝两顿。门卫周师傅指给我看小区门口角落里的白色编织袋,扒开袋口处的落雪,里面是一些泡沫板、废纸盒,这是刘汝祥生前没来得及卖掉的废品,他放在周师傅这里,以防被小偷偷去。小区门口的垃圾桶旁,刘汝祥用来休息的小板凳还扔在那里。
周师傅记得,就在刘汝祥走前不久,他们还聊起过生死的话题,刘汝祥说,希望自己走的时候可以干脆一点,“不给子女们添麻烦”。
声明:
本文来源互联网,内容旨在传播知识,不代表本站立场。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
联系方式: